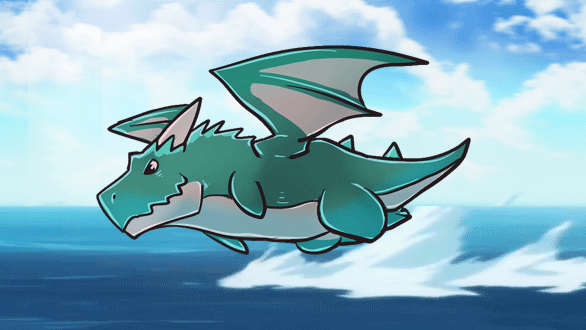生,痛苦的起點,邁向消亡的起始。
死,喜樂的終點,前往新生的開頭。
輪迴是場永恆的騙局,耗費了自己,學到永遠記不住的教訓。
但應感到幸福,為無處可逃和自作自受乾杯。
神,作為安慰的虛假存在,人在為自己做出的快樂監視下,
演一場不停換角的戲……。
─神殿內殿祭台─
用視線去歌詠,不,應是陪葬,這美麗卻又實際殘缺的,秋天,支撐著這豐饒的,正是春和夏的滅亡,啊……這氣味真令人神往呢?私底下讚頌死亡和黑暗,原是我這崇拜生的臣民不配的高尚背叛,「異教徒」這個被鮮血薰香的名詞,不可否認地在我體內被渴望著,希望能帶給自身一些變化。
劍與權杖,我還是習慣能沾沾血氣的,只有沉浸在生命消逝的瞬間,我的心才能感到安適。感覺自己的存在接近真實,是我投身殺伐的理由,但,又沒有原因的,好空洞。
「那什麼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該死,我又對自己誠實了,而人們正是害怕這樣的自我潛質,雖然不一定是和我一樣具有血腥味的,但都會用各種方式做著同樣的偽裝與再設定,無奈,和真實如此接近,卻又感到疏離。
也許總有些樂趣吧?在這停滯的時間死水中。
秋天,涼爽的讓人覺得不出遊是對它的汙辱,也正是這樣被冬天追殺的急迫,金黃的妝粉才會四散遍地吧?
只是……。
「唉,為什麼整間神殿會只剩我和一個囉哩囉嗦的傢伙呢?」在朦朧微寒的夕照裡,打盹打發了時間,也幾乎快打發掉了自己,我無聊地坐在講桌前,往腦海裡複習我昨天的胡說八道來苦中作樂,誰叫我是大司祭,信仰的事我說了算,那些神說的,不過就是另外的傢伙胡謅的謊言罷了。
「主祭……您怎把昨天講的章節前後對調還將三天前的亂混在一塊呢?這樣會誤導信眾的!」芙茨米,虔誠有餘、智慧不足的人類女修士,最喜歡在我下班後拿一堆破爛古書追問我意思,若不好好回答她,自然在她研究之後就少不了一頓說教,著實是此地第一麻煩的傢伙,可惜我沒有工作是以她為目標的,附帶一提,我只做分內事,附贈服務是不幹的。(有增加樂趣的則否)
「這就是為什麼我是主祭、妳是修士、牠們是信眾的原因了,呵呵。」我用爪子掩住臉上的無邊笑意,看著趴在桌上一堆堆沾滿像城牆一般厚灰塵的紙捲及舊書裡的芙茨米,橘紅色的瞳仁讓他也帶著幾分秋天的感覺,有溫度,卻又離溫暖有些距離。
「唉,為什麼整間神殿的兄弟姐妹都去分會整理圖書,卻只有我和這隻千年老蜥蜴在這裡留守呢?」這句話是芙茨米故意提高音量讓我聽見的,顯然是在抱怨我把整間圖書室書籍除錯和查禁的工作丟給她,但我要聲明兩點,一來我只有300歲,二來我不是蜥蜴,是道道地地的龍。(我有爪子,而非手掌,不過會站立的龍和龍人本來就難以分別)
「今天真適合出去走走呢,妳說是麼?芙茨米」我輕輕擺動尾尖,微笑觀賞芙茨米因為煩躁而分岔的棕色毛髮,還故作瀟灑地甩了我細緻的長鬃一下,嘲笑她的瞎忙。
「是是是,可是神殿不能沒有人看守,如果我們出去了……。」芙茨米元是撈叨著的,但我沒有心思聽這些,於是便將這些話腦內消音,對我來說,欣賞窗外夕陽更來的有意義。
「……。」將頭靠著椅背,舒服地瞇起眼睛的我,用食指尖輕輕碰觸喉頭的逆鱗,藉此起彼落的陣陣刺痛來溫習自己曾執行過的任務,以光箭狙殺敵將這種平凡任務已經提不起興趣了,最令我難忘的,還是上一次和目標在半空中邊墜落邊打鬥的過程,情急一刻我的逆鱗被他抓住,雖然中間過程我已經沒有記憶,但醒來張開翅膀時,看見他身上那道被利爪撕爛的傷口,全身便有著魔般的快感在竄動,至今我仍在追尋這份悸動,這無音聖歌,我崇信著。
可惜,至今還沒輪到我接委託,我只好暫時安於大司祭的身分,對於曾指導過創教人的我而言,真是無趣的緊,長久的生命,除了盡觀察的興之外,著實無什麼意義,並非一切都能改變。
而我開始進入這裡,不過是最近七八十年的事,在這個教會,永生不朽被當作最大依歸,總以為經過好幾世的不懈努力,終能破除己身的壽命限制,達到與天地同化的境界。
像顆石頭,對那頑固的思想,我下了注解。
「碰!碰!碰!」大門顯然不是稱職的傾聽者,門外似乎忽然發生了很緊急的事,外頭的生物奮力衝撞木門的寬腰,芙茨米放下書本錯愕看著門的震動。
「還看什麼?快出去迎客呀。」依照這個力道,應該不是人類或是精靈,至少是像石像怪那類的怪物在撞擊。
「老妖怪,你有病呀?我可沒辦法保證擋的住耶!」嘴巴上推拖卻因為無路可退的芙茨米,硬著頭皮脫下長袍,身著赭紅色緊身鬥服的曲線完整的在我面前展現出來。
「那你就盡力吧,洗衣板,你的後事我會幫你辦的好好的,我可是大司祭呢!哈哈。」芙茨米似乎對我的誠實相當不滿,額上青筋爆現,一圈暗紅色氣團以她為中心慢慢凝聚,這種凝聚鬥氣的方式整個教會裡只有芙茨米這僧團護衛長才會,雖然殺人的技巧及不上我百分之ㄧ,但是打倒過禁軍總教頭的身手,也許可以信任一會兒。
「去你的,本小姐解決完怪物就輪到你這隻老不死!」芙茨米右足輕點,纖細的腳掌爆發出驚人的推進力,讓女鬥士提起如貓般輕靈的身軀向空中一躍,純粹的前空翻不浪費一分勁力,距離剛好越過四排長椅到達門前,當裂石斷碑的一掌要為此劃下休止符時,從爆發的門板碎片中,一位身穿披風體型瘦小的孩童剛好倒在芙茨米的懷中。
「居然是個小鬼?連本小姐都沒有把握五掌打碎的大門,這小鬼居然用三掌就打壞了它?」芙茨米低頭看著懷裡的孩童,年紀並不大,深紫色眼眸配上白皙如嫩薑的皮膚,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他是看起來連粗布鞋也穿不起的貧窮孩子。
「救我……帶我回去……。」小孩虛弱地舉起滿是奇異紋身的細小手臂抓住芙茨米的肩膀,口中像是夢囈般地說出這句話。
「呵呵,你和它很有緣喔,它緊抓著你不放呢!」一瞬間看到孩童身上的紋身,我眉頭一皺發現事情比一開始還要更不單純,但是目前似乎沒有先處理的必要。
「喂,老妖怪!你就不會幫忙嗎?」芙茨米將孩童輕放在我坐的安樂椅上,轉頭對我就是一句。
「要我幫啥?不就是長久飢餓導致的體力不支嗎?你就先去廚房拿點麵包和牛奶給它吃就可以了。」我搖搖頭,對芙茨米的胸小無腦感到無奈。
「你怎麼看出來的?」芙茨米一臉佩服地看著我。
「這就是為什麼我是主祭、妳是修士的原因了,呵呵。」
「去你的,哼!」芙茨米嬌斥一聲,逕自往內院走去,留下趁機打盹的我和昏睡的小鬼。
─三十分鐘後─
嚼嚼嚼嚼嚼嚼嚼……小鬼的嘴巴在他被平胸女喂下第一口牛奶甦醒到現在三十分鐘過去了,完全沒有停下來的跡象,姑且不論他的胃袋是什麼做的,為了僧團在之後兩個星期能有東西可吃,我必須要開口。
「小朋友,你是從哪裡來的呢?不要怕,哥哥我不是壞人喔,才不會像那個暴力洗衣板那麼恐怖。」我瞇著眼睛蹲下來對這個淺綠色頭髮的小鬼說道,眼角餘光中芙茨米的面容十分的扭曲,不過由我無邪純真善良氣質所散發出來的光輝震懾了她,所以也不好發作出來。
「我不知道……。」小鬼停下了嘴巴,抬高一雙失神的眼眸看著天花板,我趁時觀察這孩子身上的紋身,由最外緣的部分判斷,這似乎是某種傀儡術的聯結契文,用來連接這孩子和某個術士,但會用到紋身的傀儡術,一般並不適用於活人,可這孩子居然會感到飢餓,他是屍傀儡的可能性並不高。
「真可憐的孩子,似乎是喪失記憶了呢?芙茨米,先去把你房間收拾一下,我晚上再做處理。」回去,是要回哪裡去呢?這孩子所說的是指什麼呢?看樣子只有等會兒對他施天眼法,才能一探究竟了。
「老妖怪,你的意思是……讓這髒小鬼睡在我的床上?這太超過了吧!」的確,包住小鬼身體的黑色披風底下,滿是沙塵和乾涸的血跡,濃濃的汗酸味佔據了小鬼的全身,完全是長期流浪的痕跡。
「當然要先幫牠洗澡阿,芙茨米,你真的一點腦筋都沒有呢。」
「老不死,你這傢伙……!」
「注意形象,形象啊,快去吧。」本來想到我應該要問這小鬼名字的,但是既然是傀儡,名字就只是虛假的。
「呿,你早晚會有報應的!」芙茨米心不甘情不願的拖走了那個小鬼,此時我隱隱約約聽到小鬼說出了一個名字。
「比拉耶……。」







 回覆時引用此篇文章
回覆時引用此篇文章